拼接的石厝 相守的溫情
2025-11-07 09:28:27 來源:平潭網 作者:欣桐 鄭也 文/攝秋光瀲滟,陽光灑進平潭蘆山村村民陳富惠的院子里。院墻邊,一棵三角梅長成了樹一樣的老樁,枝頭簇擁著紅艷艷的花。這座建于1967年的老厝,門牌號已有些斑駁——蘆山村蘆厝坑102號。
老人家見有人到來,趕忙進屋搬出長木凳,熱情招呼著。小院里,有幾間花崗巖砌成的屋子,每間屋墻上都有清晰的石頭與水泥拼接的痕跡。

老厝內簡樸的陳設。
說起石厝的建成,今年86歲的陳富惠侃侃而談。“我在1965年5月1日結婚。那時我在平潭蘆洋農場,愛人楊美菊在農場作業隊里當民兵小隊長兼婦女主任,我倆都吃的國家糧。”提起往事,坐在一旁的楊美菊笑說:“又說這些‘老黃歷’!”

陳富惠在菜園澆水。
陳富惠接著道:“我6歲那年,父母因病去世,前后就差一周。那時我已經記事了,姐姐也才9歲,好在還有親戚鄰居的幫襯。”他說,自己16歲應征入伍,于1965年退伍回到平潭,分配到蘆洋農場。
說話間,眾人已走到院子最左邊的偏舍。他指著那些五顏六色、形狀不一的石頭說,這些都是他從山上地頭撿回來的,撿得多就用板車拉,小點的就用籮筐挑。

石厝一角
在平潭,建房起厝是安身立命之本。只要有村落,就會有石頭厝。因島上盛產花崗巖,勤勞聰慧的先民就地取材,用石頭搭建房屋。陳富惠家的石厝與島上多數人家一樣,屋頂呈“人”字形,鋪著瓦片,瓦片上壓著青石,主要為了防風。
在陳富惠的院子里,還能看到平潭石頭厝的一大特色——“留碼頭”。這種俗稱“虎齒墻”的結構,在全國獨一無二。“以前多數人家建房資金不足,就先蓋一房一廳,剩下的房址就做成‘虎齒墻’,方便以后銜接。我家最早的一間厝是1967年蓋的。那時我們有了大女兒,為了蓋房起早貪黑,下班回來也會干到晚上八九點,總想著要有個自己的房子,一家人有個睡覺的地方。”陳富惠望著眼前的院子,語氣感慨地說,家里這幾間石厝,是他和老伴一間一間拼接建起來的。

石厝一角
陳富惠家的石厝雖不是島上典型的四扇厝,但大門的石料卻十分講究。“這大門是請外地的師傅給做的,尺寸也按魯班尺上的吉利數來,一般是2.9米高、2.8米寬,再根據房子高度微調。我們家地勢高,運東西上來費勁。所以這塊大石料打制好后,是用板車硬拖上來的。”
抬頭細看門楣,橫梁也是一塊完整的石料。在平潭起厝,正大門必須用完整的長石料,既堅固又美觀。“石頭上的細碎紋,是石匠用鏨子一下一下鑿出來的,摸上去能感覺到紋路。”陳富惠一邊說,一邊用手輕撫石面,“當年抬這塊石料,汗珠順著勞動布衣服從背流到褲腳,全身濕透。現在看石板上那些印子,就像當年汗珠摔成的一朵朵小花。”
為了養活六個孩子,這位曾經當過兵的老伯還學會了水電工技能,家里的電線水管都是他自己安裝的。院子菜地邊裝有一段水管,陳富惠的女兒陳英說:“我老爸真是個‘寶藏’老爸。他為了種菜買了水管,根據地勢安裝,還把井水和自來水的開關分開,這樣澆菜時就用井水,喝水時就用自來水。”
說起能干的父親,陳英和妹妹陳華仿佛有說不完的話,一邊說,一邊帶著大家參觀屋子。本以為只有四五間房,走進去左轉右轉,竟別有洞天:廚房、工具間、糧食間、雜物間、洗浴室、豬圈、雞舍、停車庫……一應俱全。
“這工具間放滿了他修修補補的工具,有鉗子、錘子,還有電動切割機、電鋸等。”陳英回憶,家里無論是修豬圈還是壘雞舍,父親都是主力,母親則在一旁打下手。“小時候家里不富裕,但父母親靠著自己的雙手改善生活,讓我們能吃飽穿暖,開開心心地長大。”她的講述,讓人對于這對有擔當的海島父親和溫柔慈愛的母親印象更加深刻。
“1985年,我們家買了一臺黑白電視機,花了620塊錢,在村里可是頭一家。那時候,村里的老人孩子都圍在這個院子里看電視。”陳英說。
陳華也感慨道:“父親身上好像總有使不完的勁兒。他一邊要做好單位的工作,一邊要打理地里的莊稼,還得養豬養雞貼補家用,里里外外拼盡了全力。”她說,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,家里買了一臺切面機,全村人都拿糧食來加工面條,一斤面掙3分錢的加工費。就這樣一點點攢錢,供養著六個兄弟姐妹,有的讀中專,有的上高中、考大學。
除了這些功能各異的房間,院子里還有幾條通道,轉角或通向院子,或連接另一間房,這四通八達的設計也出自陳富惠之手,房間外還延伸出了露臺。
陳華回憶,她們姐妹在北厝中學讀書時,周五放學后,鄰居同學、城里同學都喜歡來家里住,一起在露臺上睡,看星星,聽老人講平潭古老的故事。“就這樣快快樂樂地過了一個又一個周末。”
過去了三十多年的光陰,陳華的同學任梅芳說:“我家在任厝村,離得不遠,經常互相串門,真是一段美好的回憶。轉眼我們都年過五旬了,當年的陳伯成了太公,他孫子的孩子都上小學三年級了。看他依然精神抖擻,精氣神這么好,真是老有所樂!”
夕陽從村那邊的山頭緩緩落下,陳富惠從自己改造的車庫里推出一輛電動車,并給老伴戴上安全帽。這兩位加起來超過168歲的老人,準備騎車去中樓看閩劇演出。“這些年,只要聽說哪個村有演出,我爸就帶著我媽一起去看。我們支持他們做自己喜歡的事,只能一再叮囑‘慢點,注意安全’,就像當年我們騎車上學時他們叮囑我們一樣……”陳英說著,滿目溫情。
陳富惠跨上那輛老電動車,輕快地駛出村口。晚風拂過他花白的鬢角,他的身影漸漸融入金色的光影。
眼前這幾間依山而建的石厝,石塊壘著石塊,仿佛他們一家相攜相守的歲月。石墻縫里探出的三角梅,院子里曬著的地瓜干,傍晚升起的裊裊炊煙——這座斑駁而堅實的石屋,裝著陳富惠一家熱氣騰騰的日子,也珍藏著幾代人共同的記憶。
或許某個夏夜,他們曾圍坐在天井里搖著蒲扇數星星;或許某個除夕,滿屋飄香的年夜飯溫暖了冬日的時光。這些尋常日子里沉淀下來的溫暖,讓這座石厝在時光中寫就了一家人相親相愛的綿長故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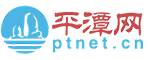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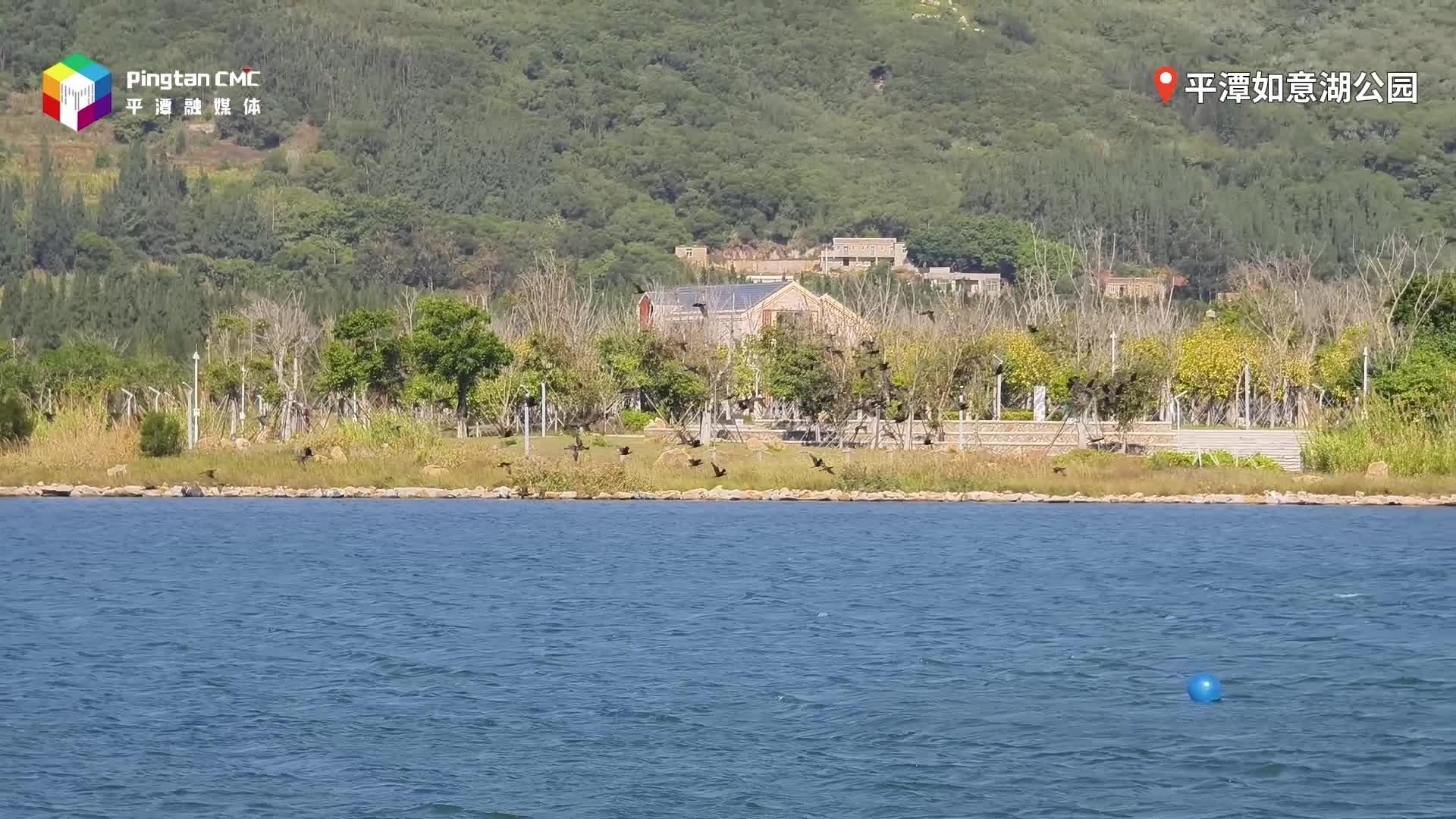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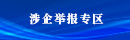
最熱評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