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傳媒大學團隊:“平潭是一座自帶電影感的海島”
2025-09-12 09:41:31 來源:平潭網 作者:王焰 文/攝平潭網9月12日訊 “三、二、一,全場靜音!”導演張博涵斬釘截鐵,海畔頃刻歸于風與浪的呼吸。錄音師馬川降桿凝神,攝影師羅啟宸果斷開機。這是中國傳媒大學團隊參賽作品《離島》的拍攝現場。鏡頭中,陽光潑金,海面如綢。男女主角沿堤壩行走,老式自行車緩緩伴隨,遠處風車如時光緩緩流轉。為這一刻,團隊已堅守了數個小時。

藍調時刻的拍攝現場,海上風車在靜靜旋轉。
“卡!過了!”張博涵一聲落下,團隊成員相視無言,笑意浮動。他們腕間粘滿汗水與灰塵的黃色膠帶,也在這一刻熠熠生輝。“72小時極拍”首日,他們終于等到那束光,與平潭的故事真正相遇。

《離島》在拍攝中

團隊成員合影
“守島,也是一種向外生長的姿態”
“平潭是一座自帶電影感的島嶼,它的風景里藏著情緒。”20歲的導演張博涵望向遠處的大海,輕聲說。來自陜西西安的他,已是第二次踏上平潭島。第一次,他來到大福村感受古村人間煙火;而這一次,他帶著鏡頭與故事而來。
當拍攝團隊行走于白青鄉豐田村的海邊小路時,某一刻,恍若推開了時空之門。“那一瞬,我好像走進了臺灣導演侯孝賢的《戀戀風塵》電影之中。”張博涵眼中閃過光亮,“呼吸著略帶咸濕的空氣,我一下子想起一個關于暗戀的故事——青澀、朦朧,卻足夠真摯。”
于是,《離島》悄然誕生。影片將時間錨定千禧年初,講述一對在平潭長大的青梅竹馬——女孩決意離島追夢,男孩選擇留下守家,彼此心存悸動卻終須告別。臨行前,男孩為女孩放映了《戀戀風塵》,讓電影代替大海,陪她遠行。
這部短片既是青春紀事,也是一代人對“離開與堅守”的思考。透過《離島》,他們想呈現一座島的體溫,也道出年輕一代的銀幕鄉愁。“最觸動人的是放映戲。”聯合導演苗宸緒說,“他不是在挽留,而是想讓她記住:無論走到哪,故鄉有影像可循,有記憶可回。”
為貼近土地呼吸,團隊大量采用平潭方言臺詞。在范博涵看來,方言不只是一種語言,更是一種情感載體。“那一句句‘地瓜腔’,一出聲,就是家鄉。”
《離島》不僅致敬了侯孝賢,也向希臘電影大師安哲羅普洛斯汲取意象范本。“我覺得平潭的海上風車能拍出安哲式的詩性。”范博涵用手比劃著,“你看,它們安靜地轉動,就像情人之間未說出口的情緒,終歸于靜默。”
“男主的選擇并不封閉,島嶼是橋,矗立在海上,連接了陸地與海洋。守島,也是一種向外生長的姿態。”張博涵說。

平潭白青鄉豐田村的海灘是《離島》取景地之一。
等光來,等故事真正發生
九月的海島,清晨六點,海風中帶著一絲涼意,拍攝團隊已經出現在平潭島北部的一處海岸線取景地。羅啟宸仔細擦拭著鏡頭,目光不時關注著天際線的變化。今天是拍攝的關鍵日,他們需要捕捉男女主角在堤壩上離別的戲份,而這一切,完全依賴于光。
“我們想要的是那種金色傾斜的光線,既溫暖又悲傷,就像這個故事的氣質。”張博涵反復查看取景器。然而,海邊的天氣并不配合,太陽逐漸升高,海面反射出刺眼的白光,完全不符合他們預設中“柔軟而憂傷”的視覺基調。
時間一分一秒流逝,整個團隊進入了一種焦灼的等待。馬川不斷檢查設備,生怕海風帶來多余的噪音;范博涵一邊確認接下來的拍攝動線,一邊安撫著演員……潮水慢慢漲起又退去,遠處,海上風車田發出低沉的旋轉聲。
“等光,其實也是一場考驗,考驗著你的耐心與對電影敘事的信任感。”羅啟宸后來在采訪中說。坐在礁石上,他把鏡頭始終對著海平線。云層時而密集,時而散開,光線在海面上不斷變幻:銀白、淡金、淺灰,像情緒一般流動,但這些始終不是他們想要的那一種狀態。
就在等待的過程中,張博涵和苗宸緒也沒有停下。他們利用這段空白時間反復和演員溝通角色,甚至臨時調整了幾句對白,讓角色的離別情愫更貼近方言的韻律。“平潭話中有很多語氣助詞,‘咯’‘嘞’‘喏’,放在不同的位置,情緒就完全不同。”張博涵說,“等光的時候,我們反而把故事磨得更細了。”
一直到了下午四點半,光線終于變得傾斜而透明。整個海面像是被調低了曝光,泛起一層朦朧的金箔色。團隊迅速進入拍攝狀態。羅啟宸扛起機器,馬川舉桿收音,演員走入預定位置。沒有口令,只有眼神交匯中的默契。那一個鏡頭,一遍過。
“卡!好,就是這樣!”張博涵的聲音終于不再緊繃。海風吹起場記板上粘著的黃色膠帶,也吹散了所有人一天的焦慮。那一刻,他們等到的不只有光,還是故事真正降臨的時刻。

張博涵(左)和伙伴彼此加油打氣。
在光影交錯的記憶里重逢
一次轉場途中的偶然駐足,讓拍攝團隊與一座已歇業的老式影院不期而遇。在平潭蘇澳的海豐電影院門口,他們邂逅了老電影放映員吳正梅。得知七旬老人珍藏多年的一部老式膠片放映機因年久失修無法啟動,這群年輕人毫不猶豫伸出援手。于是,一場跨越代際的接力修復在平潭悄然展開。
“這臺1972年生產的長江牌膠片放映機,曾經點亮過無數個夜晚,現在我和它都老了。”吳正梅惋惜地說。
機器內部零件老化,鏡頭模糊,輸片齒輪銹跡斑斑。團隊圍攏過來,有人撫摸機身,有人輕輕擦拭鏡頭蒙塵,心生惋惜:“它不該就這樣被遺忘,我們試試把它修好。”
沒有專業工具,他們就靠隨身攜帶的多功能刀、膠帶,甚至零食包裝上的鋁箔紙動手。照明燈泡是從河北加急郵寄來的;斷裂的線路由馬川重新焊接;當發現膠片傳送帶無法限位時,范博涵用雪糕棍和易拉罐拉環做了一個精巧的卡扣。“小時候我就愛拆各種電器,沒想到這時派上了用場。”他笑著說。
每一天緊張拍攝結束后,團隊就聚到電影院幫忙。吳爺爺有時靜靜坐在一旁,有時會說起他年輕時放映的故事——哪些片子最賣座,如何一本一本倒片、檢片,怎樣在機器故障時用手電筒照亮字幕替觀眾讀臺詞。“以前沒那么方便,那時候看一場電影,像過節一樣開心。”吳正梅回憶說。
最后那個夜晚,當所有零件重新組裝完畢,范博涵深吸一口氣,按下開關。機器先是發出熟悉的嗡鳴聲,接著,光束從鏡頭中傾瀉而出,照亮老電影那斑駁的墻壁。
“謝謝孩子們,讓它再次看見光……”那一刻,吳正梅聲音哽咽,團隊每個人的眼里,也有光在晃動。誰能料到,他們原本是來拍一部關于離島與告別的電影,卻意外參與了一次記憶的復活。這場電影精神的傳承,成為“72小時極拍”中動人的番外篇章。
《離島》的最后一場戲,男主角為女孩放映《戀戀風塵》。海風拂過,遠處風車緩緩轉動,放映機的光束仿佛穿越時間,將一段關于等待、堅守與熱愛的影像定格成永恒。那一刻,恰似一種命運的呼應,電影之內與之外,光影交織,彼此成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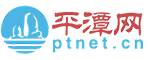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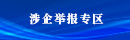
最熱評論